
編者按:2022年7月6日,由三峽川劇藝術(shù)研究傳承中心(重慶市三峽川劇團(tuán))創(chuàng)排的本土原創(chuàng)現(xiàn)代川劇《峽江月》登上第五屆川劇節(jié)舞臺。該劇是重慶市近年來新創(chuàng)川劇的代表劇目之一;是“萬州戲劇現(xiàn)象”的又一亮點(diǎn);是聞名遐邇的“下川東”川劇藝術(shù)傳統(tǒng)的再度轉(zhuǎn)身與亮相。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(xié)會邀請文化評論者和部分觀眾參與本劇的觀評活動,他們將從劇目緣起、文化背景、藝術(shù)特色、呈現(xiàn)情況等方面,對本劇進(jìn)行介紹和討論。
歷史深處的“守護(hù)”——川劇《峽江月》的詩意表達(dá)
文/趙勇
這一晚,我在川劇《峽江月》的高腔中,恍惚間看到了秦嶺的山和江南的水。與西方戲劇的“史詩”筆法相比,中國戲曲“花部”中的“南腔北調(diào)”,簡直妙不可言。人們用歌舞演故事,用命運(yùn)傳真情。

我一直相信,戲劇是由一方水土雨露經(jīng)年化育而成,那是生活在這里的人們與天地萬物的對話,《峽江月》就是如此。故事的發(fā)生地原四川萬縣,現(xiàn)在的三峽腹地重慶萬州,蜀道之難、生存之艱、世道之苦并沒有摧毀彼時(shí)人們的生存意志和對幸福的向往。茶館老板江小月,接連痛失三個(gè)有恩有義的男人,不斷跌倒爬起,收拾心情,在戰(zhàn)火和生活的摧殘中繼續(xù)守護(hù)和追求真愛。他們的情感接力,經(jīng)得起考驗(yàn),愛得坦坦蕩蕩、活得瀟瀟灑灑;他們茶館互助,國難當(dāng)頭,激流勇進(jìn);他們走峽江、望明月,豪情萬丈、柔情似水。
《峽江月》中有愛情之悲,但不撕心裂肺,有愛情之媚,但不無病呻吟,因?yàn)檫@一切和大歷史、大山水有關(guān)。所謂大歷史指的是,故事愛情中的悲歡離合,是小人物在歷史航船中的顛簸。大山水指的是在峽江地區(qū)生活的人們有一種天然的戰(zhàn)山斗水的頑強(qiáng)生命力。在抗戰(zhàn)和內(nèi)戰(zhàn)期間,萬縣都是連接江漢平原和四川盆地之間重要的戰(zhàn)略交通重鎮(zhèn),全國各地人員往來頻繁,在此落腳生息。江小月經(jīng)營的茶館和水老大從事的碼頭航運(yùn),都是非常典型的巴蜀公共空間。江小月的前夫死于日本大轟炸,而水老大冒險(xiǎn)轉(zhuǎn)運(yùn)抗日物資,為國犧牲,既是愛國也是愛家,他對江小月守望十二年。江小月喜歡鐵骨錚錚的漢子,稱水老大為真男人,既是一種兩性之間的情愛流動,也是對慷慨赴國難的英雄的愛慕。內(nèi)戰(zhàn)爆發(fā)后,茶館老表劉望成了有待“成長”的角色。劉望膽小怕事,他自知無法入江小月的眼,但依然默默守護(hù)茶館這個(gè)“家”的完整性和可持續(xù)性。在他看來,只要茶館這個(gè)物質(zhì)基礎(chǔ)在,生活就會繼續(xù),家就沒有散。所以茶館凋零,他不離開,茶館被賣,他竭力反對。劉望把這個(gè)望江茶樓看成是與江小月“相守”的見證。當(dāng)反動勢力丘八威逼江小月說出劉望的下落并強(qiáng)搶茶樓的時(shí)候,劉望在完成護(hù)送船幫孤兒的任務(wù)后回來了,并最終為救江小月死在丘八的槍下。在那一刻,他聽到了江小月對他的贊美,成為了真正的男人。編劇鄭瑞林曾在去年成都舉辦的川劇創(chuàng)作與評論研討會上作了《紅色題材的詩意表達(dá)》的發(fā)言,“紅色題材劇作不一定全部聚焦于革命領(lǐng)導(dǎo)者或者聲名彰顯的人物,普通百姓的歷史及命運(yùn),同樣具有動人心魄的力量”。這些小人物的革命光輝,并不完全是完全“天下為公”的家國意識,而是有一種底層視野下的私人情感在起作用。他們將革命化為一種溫暖的注視、情感的守護(hù)和相互之間的惻隱之心。比如水老大和劉望這兩個(gè)男人他們“一明一暗”“一里一外”,前者滿嘴“開黃腔”大膽表達(dá),保護(hù)小月不被欺負(fù),后者“酸溜的”說話,小心翼翼照顧。這種愛情不是建立自私自利的對愛的嫉妒和占有,而是有以一種樸素的古禮之美。還有來自上海的小茉莉,被江小月所收留,原因之一自然是江小月的抗戰(zhàn)意識的自覺,因?yàn)榻≡轮佬≤岳驅(qū)びH的對象是國軍抗日戰(zhàn)士,更重要的是她底層姐妹的同情和關(guān)愛,同是天涯淪落人。

《峽江月》的“川味”不只體現(xiàn)在萬縣人民敢愛敢恨的鮮明性格、家國一體的豁達(dá)胸襟,還流轉(zhuǎn)于其獨(dú)特的審美“韻味”上。該劇采取的悲劇喜演的表演方式,既有孤苦無助時(shí)鏗鏘有力的時(shí)代控訴,也有纏綿悱惻的愛情試探。比如當(dāng)她和水老大的愛情被傳統(tǒng)封建家長三叔公阻撓被當(dāng)眾羞辱、圍攻,仍不甘命運(yùn),聲聲泣訴。當(dāng)他被逼著去退聘禮,兩人眉目相送,互相愛慕對方,又要恪守禮數(shù),這個(gè)時(shí)候,用了角色自白的方式,互相唱出自己的心里話,讓觀眾知道各自的情感顧慮。這樣一種互猜心思的感覺,像極了昆曲中情竇初開的戀愛橋段。
本劇主角江小月的扮演者譚繼瓊,扮相俊美,嗓音甜潤,唱腔明亮而溫婉。哭訴的時(shí)候,川劇高腔傳遞出一種有力量的美感,她思念自己所愛的人,但卻“哀而不傷”,還有活下去的決心。譚繼瓊是戲劇梅花獎得主,近年主演的《鳴鳳》《白露為霜》等川劇作品備受戲劇界矚目,這些作品都將女性提升到一種主體性視角,刻畫出四川女性剛?cè)岵?jì)的性格和對獨(dú)立人生的主動性追求。川劇花旦高腔“宛轉(zhuǎn)”而不低靡,氣息在疾徐間回旋上升,從鎖眉低吟過渡到清澈見底的高音,然后迅疾消散于舞臺上空。這種腔調(diào)的“突轉(zhuǎn)”仿佛是女性主人公對自我生命價(jià)值的一次確認(rèn)和回歸。
水老大等船工在運(yùn)送戰(zhàn)略物資中遭遇日軍大轟炸壯烈犧牲,這一場景讓人印象深刻。這一段將川江號子的“喜劇”精神融入到悲壯的歷史語境中,從容傳達(dá)出水老大等中國底層人民英雄主義氣概。川江號子用四川話演唱,演唱富于激情,發(fā)音硬挺洪亮,吐字清晰有力,強(qiáng)調(diào)字頭噴口,音色堅(jiān)實(shí),節(jié)奏自由而又符合勞動規(guī)定節(jié)拍。船工號子由號工領(lǐng)唱,眾船工幫腔,號令而歌。每句領(lǐng)腔都要“喊”起來,而且每句掃腔都要給船工的幫唱一個(gè)“喲呵呵,嘿咗”。我們能感受到在滔滔江水和高空盤旋的日軍飛機(jī)的轟炸中,這些船工們一鼓作氣劃槳向前沖鋒的場景。水老大領(lǐng)唱,“峽江兒郎血滿腔”“闖得過去地久天長”“闖不過就如夢一場”,其他船工以“喲呵呵,嘿咗”跟隨幫腔,要求大家同仇敵愾、不畏生死。這種一唱一和,急速推進(jìn)的聲浪,在一聲劇烈的爆炸中戛然而止,這是一種自我力量的超越,也是率性而為的男性氣質(zhì)表達(dá),具有非常震撼的陽剛之美。川江號子高亢粗獷、婉轉(zhuǎn)悠揚(yáng)、風(fēng)趣幽默。水老大面對生死時(shí)刻,想起了婆娘,想起了江小月,這時(shí),他唱到“家鄉(xiāng)親人如想我”,然后大家集體喝酒,緊接著眾船工一起唱“各人都有心頭肉。”非常俏皮的語言,講出犧牲者內(nèi)心的不舍和迎接犧牲的達(dá)觀。

《峽江月》的舞臺前景兩側(cè)分別是江亭一角和盤根交錯(cuò)的黃桷樹,地域符號簡潔生動:望江亭是一種守望,望眼欲穿的等待,那也是劉望的隱忍和堅(jiān)持;黃桷根系讓人聯(lián)想到一種生死相依的命運(yùn)糾纏,江小月念念不忘的好男兒魂安于此。舞臺主空間承擔(dān)敘事功能:幾把竹椅,幾張方桌,幾盞清茶,幾度春秋。四川茶館,別具一格。這里鄉(xiāng)音裊裊,川民生活氣息撲面而來。這個(gè)茶館被置于活動裝置中,分別由兩側(cè)向中間緩緩移動,并拼貼為一個(gè)整體,隨后故事徐徐展開。這使得茶館成為一種陌生的熟悉場域。望江茶館發(fā)生的戲劇性事件被披上一種歷史真實(shí)的外衣,我們熟悉的“茶館”味道沒有改變,同時(shí)也帶來一種“新奇”的現(xiàn)代觀劇感:舞臺裝置打破幻覺,讓我們依然需要一種冷靜的距離去審視那個(gè)歷史褶皺下底層人們的真實(shí)的生存境遇。這個(gè)茶館中包蘊(yùn)的東西依然需要在當(dāng)下繼續(xù)燃燒。
舞臺后景中是一幅奪目的巨幅紗帳,上有一輪圓月,透過紗帳后面是崇山峻嶺下朝我們奔來的洶涌峽江。臺下的觀眾,透過朦朧的紗幕,目睹了以江小月、水老大為代表的川江人民,在歷史深處的真情守護(hù)和生生死死的民間傳奇。
作者:趙勇,系藝術(shù)學(xué)理論博士,重慶郵電大學(xué)副教授,重慶文藝評論家協(xié)會會員。
(本文照片由余小武拍攝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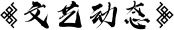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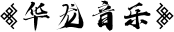
600bd524-6a81-498b-8e10-6aff1cc18895.jpe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