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瞿塘峽第一重門——夔門,離奉節縣城二十余里,兩岸斷崖壁立,高逾百丈,寬不及百尺,深峽水急,驚濤如雪,自古便有“夔門天下雄”之盛名。宋代陸游曾歌吟:“憶到夔門正月初,竹枝歌舞擁肩輿。”唐代杜甫亦嘆曰:“眾水會涪萬,瞿塘爭一門。”人們習慣將夔門與瞿塘峽同稱,生于斯長于斯者,對夔門無不懷著天然純樸的敬愛,對瞿塘峽依然眷戀著自然天真的記憶。
年少時,曾與幾位同窗相約游瞿塘。沿陡峭古棧道,雖一邊絕壁,一邊懸崖,但卻信步而行。行至風箱峽,迎面石壁之上,“風箱峽”三個白色大字赫然醒目。彼時年少懵懂,大家指壁爭論不休,最后只得望文生義:瞿塘峽便如風箱一般,自夔門至風箱峽,水流奔騰,急浪擊石,俗語道“水生勢,勢成風”,風箱峽自然吹出了夔門風來。那時的江水,黃濁如泥,波濤洶涌,漩渦狂卷,驚濤拍岸,氣勢逼人。船行其間,汽笛高鳴,風勢洶洶,風聲颯颯,風嘯厲厲,夔門的風掃過臉龐,仿佛挾帶著悲涼、蒼莽、無奈與苦澀;風中凌亂,又似裹著淡淡憂傷與惆悵,向人無言傾訴著夔門兩岸猿聲哀嚎、兵戈交加、詩情畫意的往昔傳說。
如今再立夔門關遺址之前,風箱峽早已沉入浩浩江水之中,化為歷史深處模糊的印記。眼前江水,漫江碧透,平緩如鏡,細浪輕吻著岸邊,水鳥悠然嬉戲于水天之間,青山倒影如畫,白云輕浮蕩漾。此刻夔門之風拂過面頰,只覺水勢安詳,風亦溫柔:風勢和煦,風聲柔然,風語徐徐,似帶著一縷溫柔、一絲甜蜜、一片香氣,一陣舒心。風生水勢,水亦成風,八公里瞿塘峽中,清風徐來,悠然彌漫于天地之間,亙古如是。
夔門,乃一座古老神奇之門,是大自然慷慨賜予的天選之門,鬼斧神工雕琢的天然杰作,滄海桑田孕育的天機巧構。夔門既是自然的江水之門,則必然賦予了“門”之真義,亦自然生成了夔門之風。宋玉《風賦》曾云:“世間萬物之風,有大王之風,亦有庶民之風。”而夔門之風,卻道是天地自然之風,淡然閑適,悠然自得。在這拂面的美好風中,每個心靈深處都充盈著希望與美好。
時光流轉,當我再次走進夔門,抵達瞿塘峽深處時,過往一切歷歷在目,親切而感動,悠然而眷戀。故鄉山水依舊親切美好。古人云:“觀山則情滿于山,臨水而意溢于水”,山水正是孕育生命的搖籃。夔門雖失往日之雄奇險峻,水亦退卻了昔時湍急激蕩;今日夔門卻添了幾許凝重溫婉,江水亦增了幾分柔情深遠。自然萬物,眾生皆在有無之間,得失之果;我們臨此凝聚著天地鬼斧神工的夔門,正如開啟一扇窗扉——上帝便同時為你打開了另一扇門,那門通往真誠永恒,通往你精神的空間與靈魂的殿堂!
??門的風,有著獨特山水之心,有著強烈地域之靈,更有著詩情的境,更有著人性光輝的魂。風過夔門,吹拂八公里瞿塘,悠蕩于天地之間——此風早已吹透古往今來,亦必將吹向渺渺未來。風是歷史卷動的書頁,是滄桑與溫存交織的永恒呼吸;風拂過這扇天造地設之門,吹徹八公里峽谷,也吹開我們心頭通往永恒的門扉:當夔門成為記憶的起點,風便引領著靈魂,歸向那廣闊無垠的精神家園。
夔門的風,悠哉!
(作者:羅承勇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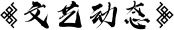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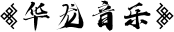
600bd524-6a81-498b-8e10-6aff1cc18895.jpeg)
